

去年11月,达赖喇嘛获得美国国会金质奖章几周之后,eBay网站开始拍卖他的老式陆虎(Land Rover)车。莎郎·斯通在Youtube网站上广而告之了这个拍卖活动。想当年,她还曾经在募捐活动上介绍达赖喇嘛是“Please(普利斯,译注:请)先生,请帮助我回到中国!”(她指的是回到西藏)。她向这部1966年产古董车的竞拍人承诺,“这是一部能为你带来快乐的车!”车子最后的竞拍价格超过了8万美元。曾经被CNN节目主持人Larry King误认为是穆斯林的达赖喇嘛还获得了Hadassah终身成就奖,由一个美国妇女犹太复国运动组织颁发的奖项。他也是唯一出现在“苹果(Apple)”广告中,并为法国《时尚》杂志担任客座编辑的诺贝尔奖得主。马丁·斯科西斯 (Martin Scorsese译注:好莱坞导演) 和布莱德·彼特(Brad Pitt 译注:好莱坞演员)也都为拍摄纪念达赖喇嘛童年的电影提供过帮助。2005,他在华盛顿举行的神经科学学会年会上发表了演讲。今年春天,他将在德国就人权和全球化等问题发言。达赖喇嘛总说自己是“一个纯粹的佛教僧人,”但他却飞遍了世界大部分地区,出镜率与小甜甜布兰妮不相上下。
正如皮科• 耶尔(Pico Iyer)在他的新书《开放的道路:第14世达赖喇嘛的环球之旅》(“The Open Road: The Global Journey of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Knopf出版,24美元)中所写,人们很容易就会想象达赖喇嘛是“电影明星和有钱人的玩物。”确实,和那些强调爱,怜悯,温和的说教,和其他无懈可击的善良事物的人一样,达赖喇嘛表现得有些无趣。“暴力滋生暴力”或“方法决定结果”这些教条听上去合情合理,但由于它们不具有理性的复杂性,因而无法发展成为一种思想体系。达赖喇嘛的英语说得很差,又总喜欢用无厘头的大笑来加以掩饰,这也让他给人留下的印象,用耶尔记录的一位记者的话形容,“他的脑袋就像个灯泡,可既不是最亮的也不是最聪明的。”(译注:把原句贴出来给大家分享呵呵,我觉得很有趣。 “not the brightest bulb in the room.” )
他自称的“纯粹的佛教僧人”的角色招致了怀疑甚至是嘲笑。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译注:传媒大亨)曾经说过,“我听到那些愤世嫉俗的人形容他是一个喜欢玩政治花样的老和尚,穿着Gucci的鞋子蹒跚前行”。Christopher Hitchens(译注:英国作家)也指责达赖喇嘛竟胆大妄为地宣称自己是“由上帝指定的世袭君主”并且在 达兰萨拉(Dharamsala)实行“独裁”,达兰萨拉是印度喜马拉雅山区的一个小镇,约有15万流亡的西藏人把这里作为大本营。中国政府一贯谴责达赖喇嘛是一个“国家分裂主义分子”,1951年,他阴谋策划叛乱,企图让解放后西藏重回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僧侣统治。许多流亡的西藏人埋怨达赖太过执着于非暴力路线,而且被西方协调者牵着鼻子走,因而没有成功阻止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完全控制。
但是,发生在近几周的事件却提醒了人们,他在600万西藏人中依然有鼓动作用。一些僧侣在拉萨进行的“达赖被逐49周年”游行活动,最后演变成了暴乱;虽然最初的游行是和平的,但是中国政府采取的激烈应对措施也是可以预期的。中国学者王利雄(注:音译Wang Lixiong)承认,“事实上,达赖仍然在西藏人的精神世界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依现在的情况看,若西藏的经济前景和传统文化因为汉族人的介入,被破坏得愈多,那么西藏人对达赖的敬重程度会随着遥远的距离不减反增。
耶尔写到“达赖喇嘛的心与灵所在之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领会的境界。”他的修行生活开始于每天凌晨3:30,日日如此,他告诉耶尔修行的主要内容就是,“冥想,俯卧,背诵特别的经文,然后做更多的冥想和俯卧,接着就是阅读藏传哲学书籍或其它的文章典籍;阅读,研习经典,周而复始,傍晚时分‘做一些冥想—晚间冥想—大约一个小时。然后,晚上8:30上床休息。’”
听起来,这个年逾古稀的僧人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冥想与阅读—更何况,他从6岁就开始这样的生活,接受了近20年足以让人筋疲力尽的佛学,藏族文化与艺术,逻辑学,梵语和传统医学教育,并最终获得了“格西”学位(大致相当于佛法与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但是佛教徒的精神修炼往往都是残酷且严苛的。“持之以恒”是佛祖的遗言,即使是达赖喇嘛也不可能达到智慧和平静的最高境界。达赖近似神话的童年故事使他的地位超越了大部分的凡人。1935年,他出生在远离拉萨的一个农民家庭,两岁时,一个来自拉萨的僧侣团找到了他,认为他可能是刚圆寂的13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在五花八门的征兆中,拉萨东北方向的天空中挂着的数道彩虹提醒了这些僧人下一任达赖喇嘛的所在。1939年,经过一系列庄重的仪式,这个孩子离开了老家由泥石砌成的房子,被恭迎到了拉萨,并成为布达拉宫,这个如谜般神秘的宫殿理所当然的掌管者。
达赖喇嘛通过临摹13世达赖的遗嘱来学习书法— 这份遗嘱由于它神奇的预言性,成为了西藏历史上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文献。它写于1932年,当时的西藏在与他东边强大的邻居不自在地共存了几个世纪后,正享受着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那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之间的内战还未结束,输赢未定。不过,13世达赖喇嘛却预感到西藏短暂的自由将很快会被毛领导的“红色共产主义者”粉碎。
即使达赖喇嘛知道了这些预言,他还是无能为力。在布达拉宫里,他的生活就是与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勾心斗角做斗争,这些内部争斗彻底葬送了他的几位前任,并且让西藏的弱点在它的邻居面前暴露无疑。第9,10,11,12世达赖喇嘛均早夭,传言说他们系被人投毒致死。第13世达赖喇嘛,在躲过了身边亲信策划的一次暗杀后,认识到他那如孤岛般王国相对于现代世界那些高度组织化的帝国和单一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何其脆弱。但是他改善西藏行政管理和提升军队建设的计划遭到了高级僧侣的极力反对,因为他们蛆虫般的生活完全依附于西藏腐朽的农奴制度,没有农民们劳动创造的粮食和上缴的税金,他们将无法生存。所以,为了维护自己在农奴社会的统治地位,他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残酷的政治斗争中。1934年,13世达赖死后不久,改革派政治家Lungshar就被施以一种古老的藏族刑罚—将两头牦牛的膝盖骨顶在受刑人太阳穴上将眼球挤爆--折磨致失明。
1947年,当一群僧侣朝着西藏驻军大呼小叫,寻衅滋事时,11岁的达赖喇嘛正拿着望远镜从布达拉宫观看着这一切。这场由于他的前幕僚被捕而激发战斗延续了几个星期,导致数十人丧生。最后,1950年时他以达赖喇嘛的身份夺取了西藏的管治权,尽管没有获得任何方面的承认。但是,他几乎还没有时间去注意他的前任对藏族人的冷漠做出的警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了占领包括西藏东部在内的中国所有地区。10年后,达赖喇嘛和成千上万的西藏人被迫开始流亡。
达赖喇嘛向他的西方听众强调的重点是,他已经开始融入现代世界—他正在努力扭转错误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在加强对科学和民主治理的学习。而正是这些理性的学习历程激起了耶尔的兴趣,作为一个小说家,旅行作家和《时代》杂志的撰稿人,耶尔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们历史这一刻的黎明“所有文化之间都是共通的。”他把达赖喇嘛认作是老对手在新旧时代相遇,东西方文化碰撞产生的振奋人心的产物,他的存在刺激了世界上其他许多固守传统思想的人,使他们投入到了一场保护传统的运动中去。
“在西藏,达赖喇嘛是旧文化的化身,是与世界割离的,为古老的甚至是消失的传统主义代言,”耶尔写道。“现在,流亡中的他又是新文化的化身,好像仅仅只用了50年就完成了对过去800年历史的巡礼,带着他特有的率真,走向未来的怀抱。”耶尔列举了一大堆证据来证明达赖喇嘛的前瞻性计划。这个藏族人的领袖对他如神般的血统表示怀疑,承认在签名认可奥姆真理教(其成员在东京地铁站释放了沙林毒气)创始人时太过草率,从而证明他并不是一个“活佛”。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佛教徒,却建议他的西方追随者不要信奉佛教。他满怀热情地寻找著名的科学家,宣称那些被现代科学证明错误的佛教经典应该被废止。
当达赖出现在西方听众面前时,他更喜欢讨论“世界性的道德规范”而不是深奥的佛教涅磐理论。毫无疑问,那些美国中产阶层利用周末闲暇时间聚集中央公园听他演说,他可不想把他们排挤在外。但是,正如耶尔指出,这其实也是对佛教哲学观点的一种新的诠释方法,即,所有的存在间必有其联系。事实上,也正是这种观念让达赖喇嘛很早就领会了人类社会全球化将会带来的存在主义和政治上的挑战,比气候变化灾难对这些挑战作出的警示早了几十年。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译注:国际著名政治理论家)于1957年写到,“人类历史中第一次,地球上所有的民族拥有一个共同的现在。。。。。国与国间息息相关,而且每个人对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事情都有着身临其境的感受。” 阿伦特害怕这种新“世界联合体”如果缺少一种精神可能会演变成一种极广泛的消极氛围,这种精神就是“舍弃,不是舍弃某国的传统和历史,而是舍弃传统和历史标榜的权威与普遍正确性的约束。”
作为600万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舍弃传统--不论是在维护私利的保守政治还是宗教—的权威性方面均作出了贡献。这正是他的影响所在,过去的几周,他只需发出一个小小的号令,就在西藏引发了大规模的,还可能是无法控制的暴乱。虽然,他坚持拒绝使用暴力,认为这样的行为是违反道德,并且会产生反效果,甚至威胁,如果反中国的暴力活动继续的话,他将辞去 达兰萨拉流亡政府的领导职位。他被迫用另一种隐晦的手法指责中国的“文化种族屠杀”,但还是表示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他甚至一直以来都不赞成用相对温和的抗议方式,包括绝食和经济制裁来对中国政府施压。他认为,西藏需要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他曾经说过,“一个国家不可能独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他勇敢地普及“世界的责任”这一概念,以告诫那些希望独立的人,在他们开始对世界的思考之前,先要想想这个责任。
他说到西藏发展的倒退以及在共产党统治前自治时极为懊悔,他认为西藏的不幸在于没有为20世纪的到来做好准备。他为西藏流亡政府引入了民主宪法和法定选举。最近,他还提出了一个更激进的想法,这种想法颠覆了西藏近1000年的传统:通过选举选出下一任的达赖喇嘛。
几十年的流亡生涯中,达赖喇嘛对让西藏付出的高昂代价的政治经济孤立主义有了深刻的认识,也帮助他把 达兰萨拉变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的模范聚居地,在这里,退役的以色列青年与新来的西藏难民杂居。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件事都有些不同寻常,想想一个曾经居住在有上千个房间的皇宫里,作为一国之君的男孩,现在居然变成了“全球主义”的代表人物,耶尔的用词,偶尔有些宽泛,此处“全球主义”是指对实现迅捷的通信和舒适便捷的旅行的美好愿望和坚定的信念。毕竟,达赖喇嘛成长时与西方国家唯一的联系就是美国的《生活》杂志。(后来,他将阵地转移到了《时代》杂志和BBC)。虽然,达赖经常在亨利·卢斯(Henry Luce,译注:《时代》创办人)的周刊露面,但是他并不反对毛泽东思想。1954年在北京的访问,虽然合作并不顺利,达赖喇嘛却称中国革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为毛泽东谦虚的风度着迷,可当他与这位伟大的舵手最后一次会面的时候,却被毛的一席话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毛宣称“宗教是毒药”— 这一信仰,在接下来的20年后,驱使中国人以正义的名义杀死了几千名西藏僧人并且摧毁了大部分的喇嘛庙。
耶尔指出,达赖喇嘛1959年到达印度时,还是“一个对现代世界一无所知的人。”他直到1979年才去了美国访问,当时佛教传统很流行,但由于听众们习惯了禅宗采用轻快的方式阐述佛学,对他那种高深的纯技术性的讲道产生了理解障碍。尽管后来,达赖在美国赢得了个人最大的声誉,但他初次访问美国时,几乎没有名人出席为他组织的活动。直到1989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达赖喇嘛的西方拥趸俱乐部才开始增多。
他的声望似乎部分也借助于20世纪30年代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所传播的关于西藏的浪漫思想。这本小说叙述了几个西方人无意间来到了香格里拉,一条和谐平静靠近喜马拉雅的山谷。1937年Frank Capra拍摄的同名电影开片就是这样一句话,“在战争年代和战争的谣言四处传播时,你的梦中是否出现过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和平安全的地方,在那里,生活不再是苦苦的挣扎而是永恒的快乐?”(这部电影给了罗斯福总统灵感,将他在马里兰的总统疗养地命名为香格里拉,但是后来,缺少浪漫情怀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又因为自己的孙子,把它改名为戴维营。)尽管西藏也有它那诉不尽的血泪史,但在西方人眼中,西藏人就是一群幸福的远离现代生活的人,他们天生就拥有幸福而不用去苦苦追求。
耶尔认识到这种关于浪漫的误解对于西藏来说是一个政治难题:“这让人感觉,或者说人们更希望让它仍然是香格里拉而不是联合国的一个席位。”达赖喇嘛似乎也准备妥协。他简化和世俗化佛教教义的决定,让他比日本禅宗或者其它西藏圣人获得了更多的听众,比如阿兰·金斯伯格(译注:)的宗教老师曲嘉仲巴(译注:《西藏度亡经》的作者),他原来在西方的影响力比达赖要大。但是,要让一门古老且高深的哲学中产阶级化,就必定要在理性的严谨上做一些让步。在达赖喇嘛最畅销的书中,佛教表现为没有任何繁文缛节仪式的精神测验,但是 为了获得格西学位,学生们必须学习长达322卷的藏传佛教教规的宗教形式就严格得多了。
达赖喇嘛可以以神的名义进行道德制裁,但是有人指他为了吸引更多的听众,改变了佛教教义。达赖喇嘛推行的实用主义也是有局限的,但他对当代自由的敏锐触觉仍让人难忘。他支持所有少数群体均享有充分的合法权利,包括男女同性恋。但是,根据西藏的的传统,他仍然不赞成口交和肛交。(“因为它们并不能创造生命。”),同时他也不赞成性滥交和离婚,某些时候他更像一个家庭价值观的保守派。
他所有的妥协招来的苦难都比不上他曾经做出的某些决定。1988,他宣布了第一个决定,希望借此让西藏实现“真正的自治”,而不是要求完全的独立。在达赖喇嘛看来,既要考虑自身的利益,也要考虑对方的利益,西藏的独立,作为一个不现实的理想,没有必要与北京政府搞对抗。然而,他的这种姿态并不成功,不能说服中国政府他不是一个“分裂主义分子”,他们指责他是最近的骚乱的“幕后主脑”。同样也使许多西藏人怀疑到底是什么让达赖喇嘛在西方越来越受欢迎—主要是他在最近爆发的危机中不断重申只会使用非暴力手段的承诺— 使他在有些人眼里变成了一个懦夫。
“他为世界贡献得越多,”耶尔写到,更多的西藏人感到“糊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父亲有了他们却还要再去收养其他三个孩子。”藏族小说家Jamyang Norbu抱怨说西藏支持团体和达赖的流亡政府“失去了方向”,因为他们一直努力“重新定位他们的目标,包括环境,世界和平,宗教自由,文化保留,人权—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东西,却独独没了他们最初的目标,独立。”
达赖喇嘛一直热心地吸纳大都市的解放思想,他与创造了摩登时代的两类典型代表有或多或少的相似—逃避僵化习俗乡下人和逃避极权主义流亡者。即使这样,批评者还是认为:达赖喇嘛获得了国际大都市的公民身份,却都是以他那些无依无靠的子民为代价的。
当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西藏的未来则变得越来越悲观,它的精神领袖也越来越相信宿命论。达赖对祖先的宗教和建立单一民族国家这些排他主义者主张的放弃,可以看作是某人的反省,从他第一次抄写前任的预言时起,所能做的只是无助地看着他的王国的地标消失。耶尔充满了思想性的文章总是让人深受鼓舞,无论如何,正是他的文字让我们把达赖喇嘛想象成一个理性的,精神上的冒险家,他发掘了个体认同的新方法,并且融入了以新方式团结起来的世界。
的确,资本主义和技术发展使阿伦特的“人类的团结”理念得到了实现,但在她看来,一切已经变成了“难以承受之重”,煽动起了“政治冷漠,孤立的国家主义,或者对所有权力的拼死反抗”。西藏人现在最害怕的莫过于汉族推行的新经济和文化吸收。耶尔的书让一个来自西藏偏僻山区的男孩,用他类似阿甘的方式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互相理解以及实行大范围的自我净化的过程”—阿伦特相信,这个过程对于阻止“日益增加的相互仇视和一些世界性的由个体间对抗引起的愤怒情绪”都是很有必要的。达赖不可能为世界带来全面的相互理解,因为他还无法让中国和西藏达成共识。然而,他成为一个“纯粹的佛教僧人”可以利用的优势比起他要实现远大理想所面对的层出不穷的难题实在是少太多了。— 即使他谨遵佛祖的临终教诲,持之以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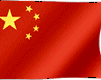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